小编:和其他创作者一样,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塔可夫斯基的复杂画面。 “复杂性”是常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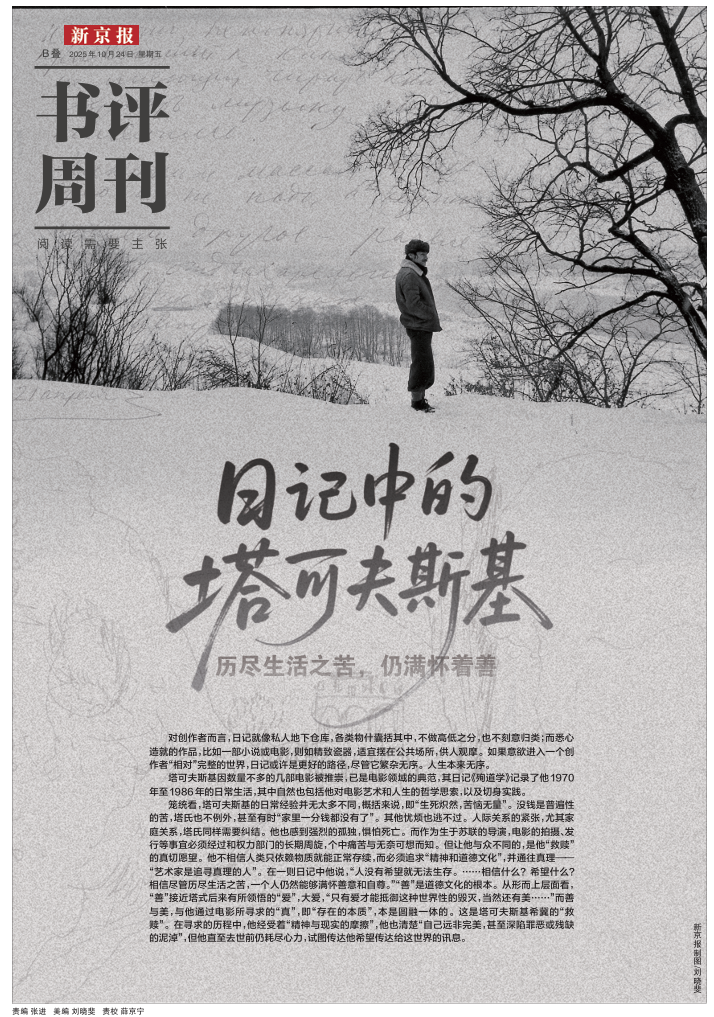 和其他创作者一样,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塔可夫斯基的复杂画面。 “复杂性”是很常见的。薄弱没有生命,没有统一。在这张图中,塔可夫斯基不仅仅是《镜子》《牺牲》等电影的天才创作者,也是一个被个人财务、家庭关系甚至生死所困的普通人。当然,日记中对“存在”的追问、对“信仰”的思辨、对“精神”与“灵魂”的探索、对人类未来奔跑路径的担忧,都与他的电影相符,因为电影是他所用的具体探索方式。也让我们看到,在平凡甚至琐碎的事情中追求“真”和“美”是可能的。本文内容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4日特稿《日记中的塔可夫斯基》B02-03版。 《殉道记: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李志芳 刘西农 版本:乌托邦|云南石油奥普尔出版社2025年5月艺术是祈祷新京报:《殉道记》是塔可夫斯基的回忆录。日记与电影不同。电影是结构完整的艺术品,而日记则支离破碎、杂乱无章。总的来说,您如何看待塔可夫斯基的回忆录?它在塔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电影、戏剧等)中有何独特性或特殊意义?李志芳(《殉道记》译者):在这里,我先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解释回忆录和电影的区别。 “人们写日记几乎都是为了总结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生的总结。”日记不像电影,是专门拍给别人看的。日记是为我自己写的。但日记迟早会有读者,尤其是名人的日记。日记的读者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让作者思考和感受的事情。读者学习的日记是自然的(书面的)并且同时创作一幅自画像。塔可夫斯基的日记是这样的。他的日记记录了他后半生所经历的苦难。这种记录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推广。毫不奇怪,名人日记的出版现在很受欢迎。在电影中,作者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新京报:“殉难”是一个具有崇高意义的表达方式。塔可夫斯基将他的日记命名为“殉道者”,这表明他对自己写的日记有一定的定位或希望。在本书的序言中,塔可夫斯基经常重复说:“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的了。”如何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塔可夫斯基在1970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对“真理”、“上帝”、“宗教”、“哲学”、“艺术”、“无限”和“超越存在”的思考。这些想法可以指出 ev每个人都追求一种纯粹的灵性,这大概就是Ta的主要思想。你如何理解塔可夫斯基?相关想法?李志芳:日记里有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的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命和责任感。艺术家的责任是关心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艺术的责任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颂扬光明。背离了这个观念,就违背了艺术家的使命,自然不会满足。也可以说,这就是塔可夫斯基的思想。然而,在体现这种责任感的意识中,似乎又遇到了困难,工作没有组织,情绪受到压抑,最后出现身体问题直至牺牲。可以说,塔可夫斯基在国外拍摄的两部电影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写照。这《怀旧》结尾时演员奥列格·扬科夫斯基手中的移动蜡烛似乎成为了他的“艺术与生活”的隐喻,而“牺牲”则隐喻了他艺术生命和他自己的终结。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塔可夫斯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属于“右”,也不属于“左”,与苏联体制完全不相容。后来他的移民经历表明他不适合欧洲的电影制作体系,他个人很难筹到钱拍电影。 1984年,即他去世前两年,他说:“……我知道,我必须把我的工作视为一种行动,一种被迫的行为。此时,工作不再能带来快乐,而是成为一种沉重的、甚至是压抑的责任。”在塔科夫的视野中,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祈祷形式。艺术的顶峰就是当你的祈祷能够亲近别人或者给别人带来帮助的时候,那么这个祈祷就是有益的。对他来说,“宗教是人类的精神核心”“殉道”是他对电影的发自内心的奉献。塔可夫斯基新京报:塔可夫斯基经常写到他创作电影的大环境对他的限制,如资金问题、失败的剧本、已完成的电影的大剪、发行问题等。1972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他们不想看到新的美丽的电影和美丽的书籍……毫无疑问,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禁忌,因为艺术是人道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杀死一切生灵,杀死它们。”所有人文主义的萌芽,无论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还是黑暗地平线上闪烁的艺术之光……他们用这种方式杀死一切,毁灭自己和俄罗斯。“塔可夫斯基创作他的电影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尽管困难重重,塔可夫斯基仍能拍出如此伟大的电影,这似乎是一个奇迹。通过厂艺委会的预算项目可以分配,也是因为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获奖了。或许因为他年轻有活力,有拿奖的资本,所以他势在必行。每当他申请一个项目时,他都希望得到领导的批准。即使个别项目申请不获批准而向他推荐另一个项目,他也不会同意。这是冲突的焦点。另外,当时还有电影制作补贴。凭借他的才华,他觉得自己一年可以拍两部电影。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一部电影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因为审查不允许它上映。这让他心里不平衡。于是,他先去找厂长,再去找局长,再去找厂长,如此循环往复,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至于他为何能够拍出这么多精彩的电影:一是他的才华;二是他的才华。其次,当时的创作环境。每部影片都经过精心制作,以免出现问题出了问题,事情就被搁置了。除了剧本内容之外,导演还投入大量精力研究镜头。无法向公众展示的isysu隐藏在镜头后面,让观众仔细思考和理解。这些东西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就派上用场了。他具有非常好的组织和指挥能力。在《安德烈·卢布廖夫》这样的大型影片中,一个人指挥数千军队与敌人作战,还有数百无数的平民。看似混乱的场面,却被导演掌控得井然有序。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总经理卡扬·沙赫纳扎罗夫日前在电视采访中赞扬了塔可夫斯基。拍摄现场涉及的人很多,但导演安排得井然有序。拍摄取得了成功,展示了塔可夫斯基的控制能力。这也是奇迹发生的原因。塔可夫斯基正在为《哈姆雷特》进行训练。俄罗斯北京失踪新闻a:在谈论一位创作者时,人们往往想了解他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塔可夫斯基与他的时代有何关系?李志芳:塔可夫斯基热爱俄罗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诗人,对他影响很大。虽然她和父亲不住在一起,而且父亲也反对她出国,但父亲仍然爱她,希望她经常回家,不忘家。塔可夫斯基对母亲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无论她出国之前还是之后。俄罗斯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在日记中,我们经常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喜爱之情。作品中总能看到俄罗斯的影子。可惜他落后了一点。如果当俄罗斯实行改革时他还活着,也许他会回到俄罗斯。新京报:从大环境到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生活状况。日记里有很多相关的内容,这使得日记日记特别而有趣。与现在大导演的想象(如名利)不同,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生活相当不愉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记中经常写到债务问题。塔可夫斯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在他的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写到“孤独”的感觉以及他与家人的关系。李志芳: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塔可夫斯基的工资和收入和其他人一样,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相似的,但他的负担很重,显得很拥挤。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拍的电影不多,他得到的补贴就会更少。这也是他经常要求导演给他项目的原因。因为。而且,他在乡下买了房子,不能拒绝钱,所以他经常借钱。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和普通人一样,每天过着简单的生活,从不铺张浪费。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他渴望出国拍电影。他一直认为在欧洲拍电影更容易赚钱。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欧洲和俄罗斯的电影投资渠道不同。俄罗斯是国家资助的电影,所以当《潜行者》电影拍摄出现问题时,国家出钱重拍。意大利高度依赖机构和私人资金来筹集投资资金。如果找不到投资,就很难拍摄项目。因此,塔可夫斯基只要在意大利有空闲时间,就会拍旅游片和纪录片,赚取外快养家糊口。说到他和家人的关系,日记里写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自从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他的父母就有了一些意见。为了不激怒父亲,他很少去看望父母。但如果不去,他就放不下,心里还是紧张。出国前我去看望了我的父亲。两人聊得很开心。似乎过去的耻辱都解开了,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至于卡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我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来理解他的。他确实是一个人,而且以他的天赋和能力,他很少尊重任何人。片场里,除了导演,没有一个不是他玩过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有多少人会喜欢他?在家里,妻子关心他、照顾他,儿子疼爱他,这让他很幸福,很幸福。他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也很爱他,这让他很幸福。质疑新京报存在:塔可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艺术家”的定义相当一致:艺术家就是追求真理的人。这个定义是一种结合“真”与“美”的表达方式,与很多现当代艺术创作者不同。如何从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理解他的意义呢?刘信农(《殉教》译者)):我认为塔可夫斯基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实践”很重要。他认为艺术家的使命是揭示存在的本质,而不是追求形式或感官愉悦。 《镜子》中屋顶落下的水、《牺牲》中燃烧的房屋、《怀旧》中雾气中的日出、意大利教堂废墟中出现的俄罗斯乡间别墅等场景,显然不是为了营造视觉奇观——影片中经典的长镜头、大量自然元素的运用,以及它们给人们带来的时间延伸和空间交错的幻觉,都是为了剥去幻觉。 并让观众面对存在本身。塔可夫斯基在日记和创作对话中都强调,艺术是对事物的质疑,而电影美学和技术是传达这种质疑的工具。在他的形象中,“美”从来不是与“真”对立的形式或表象,而是通向真理的一种方式。新京报:虽然塔可夫斯基致力于创造只能通过电影媒介展现的东西,他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日记中记录了他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托马斯·曼、黑塞、松尾芭蕉、蒙田、布宁等人作品的感想,甚至摘录了一些段落。另外,塔可夫斯基的父亲阿尔西·谢尼·塔可夫斯基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对塔可夫斯基影响很大。文学给塔可夫斯基和他的电影带来了什么?刘新农: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提到了无数作家的作品。除了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巨著文学之外,他还得到了许多西方作家的强烈认可。我想单从艺术形式来看,文学无疑为他的形象叙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道德和宗教困境实际上是《安德烈·卢布廖夫》、《太空》和《S》等电影中探讨的主题。《怀旧》中的主人公戈尔恰科夫总有一种孤独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同;而《镜子》则通过非线性的结构呈现出内在的意象和章节式记忆的短片段,或许与蒙田的随想曲或芭蕉的俳句有一些美妙的呼应。 《镜子》直接记录了父亲亲口提到的那首诗,诗中的语言节奏、重复的句子和象征意象也奠定了影片的叙事节奏。我在读日记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的阅读选择和喜好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在莫斯科,当电影创作和发行受阻时,他会反复阅读黑塞和 其他;后来离开苏联旅居意大利,登记为果戈里党员。他借的第一套书是十月革命后被流放到巴黎的布宁的日记和回忆录(老塔在日记中评价布宁:“他的小说能表达如此深沉的爱、同情、无奈和绝望”)。我想,他与其说是在这些作家身上寻找创作灵感,不如说是想从这些作家的人生轨迹中窥见自己的命运。塔可夫斯基年轻时。新京报记者:谈到塔可夫斯基的阅读,塔可夫斯基在1978年的一篇日记中列出了一份有趣的书单,其中包括《灵魂的科学》、《灵魂的不朽》和《印度哲学》。 1981 年的一篇日记写道“探索奇迹”。这些书可能暗示着塔可夫斯基精神世界的一些特征或者理解,或者他的一些激情和探索。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些特质或倾向对他在影片中的表达有影响吗?刘新农g:塔可夫斯基始终对探索强大的维度和精神知识抱有强烈的热情。我认为他试图找到一种意识形态框架来解释并体现人类的终极关切。这种阅读或许让他对自己的非理性经历更加敏感,帮助他专注于与日常生活并置的非凡经历,并最终将奇迹、救赎和宗教信仰形象化——比如《潜行者》结尾处通过视野移动事物的小女孩的轮廓,以及亚历山大为避免世界末日而进行的祭祀仪式“牺牲”。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电影是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灵魂的命运以及救赎的可能性的媒介。这些书可以强化他对电影作为精神探索工具的信念。双重疏离 新京报:日记显示,当塔可夫斯基思考救赎和上帝时,他会写诸如“爱到爱”之类的观点。有趣的是,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人时,有时会认为别人“浅薄幼稚”、“虚伪”、“不入世”、“平凡”、“平庸”等等。这不是对塔可夫斯基的批评,而是日记中呈现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刘新农:这种冲突在他的电影中确实可以看到,主角愿意为世界牺牲自己,但每天却很难与家人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对周围一切都抱有严格标准的艺术家性格中内在张力的一部分:他把“爱”视为他必须对他人承担的道德义务,几乎是一种宗教戒律。然而,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和零容忍的思维,让他对“世俗”的现实过于敏感,因此在人际关系中很难摆脱失望或疏远的感觉。日常生活。新京报:如今,塔可夫斯基已被众多电影爱好者推崇至高位。他在 1981 年的日记中说道,“我仍然不明白其他地方对我的重视:意大利、法国,尤其是瑞典。他们对我表现出非凡的尊重,并对我表示连我都无法表达的赞美。为什么我不想为自己的重要性感到羞耻。”如何理解塔可夫斯基对赞扬的反应是什么?刘新农:他对外界赞扬的反应很复杂:他知道自己作品的分量,但他也不想被媒体塑造成“大师”。因为赞美和咒骂对于固定一个探索某种符号变化的创造者来说都很重要。塔可夫斯基的内省性格,加上他作为特殊历史和政治环境下的苏联艺术家的身份,也许是这些国际荣誉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 - h他不想让外部叙述和公共话语剥夺他在创作中所享受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新京报:1983年,身在罗马的塔可夫斯基写道:“你无法在俄罗斯生存,你也无法在这里生存……”这似乎表明塔可夫斯基在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某种问题。他为什么这么说?刘信农:塔可夫斯基晚年的“流放”不仅是政治性的,还伴随着文化和身份的撕裂——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压制,但西方的唯物主义却被带到了他的身边。 《乡愁》中戈尔恰科夫离开意大利,也是塔可夫斯基本人所经历的双重戒备的写照。我认为他的“小镇”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能够容纳精神传统和理想信仰的乌托邦。但东方或西方可以提供这样的土地。塔可夫斯基的画作,上面写着“我永远不会看到的房子”。新京报:在在本书附录的采访中,塔可夫斯基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我更喜欢通过隐喻来表达自己……与符号不同,隐喻没有固定的含义……隐喻更像是存在本身,是一个包含在自身内部的整体。如果你触碰它,它就会立即崩溃。”你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寓言”的含义?他的电影教会了我们什么?刘新农:在我的想象中,他的所谓“寓言”就像一个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像大雨、火、空中生长的草木、烦人的水波。影片中的自然元素所传达的丰富内涵就是自然本身。它们是存在的方式,一旦它们变得过于有趣,它们就会失去巨大的吸引力。这种“一碰就掉”的特点,要求观众放弃逻辑拆解,转而凭直觉去体验。他不希望观众将他的电影视为待破解的密码,并贴上清晰的标签每个图像都有意义。相反,他希望观众让自己沉浸在图像的流动中,体验屏幕上呈现的一切作为一种存在,并接受自己被图像和声音的节奏所消除的存在感和精神震撼。撰稿/编辑张进/校对/龚兆华/薛景宁
和其他创作者一样,塔可夫斯基的日记为我们呈现了一幅塔可夫斯基的复杂画面。 “复杂性”是很常见的。薄弱没有生命,没有统一。在这张图中,塔可夫斯基不仅仅是《镜子》《牺牲》等电影的天才创作者,也是一个被个人财务、家庭关系甚至生死所困的普通人。当然,日记中对“存在”的追问、对“信仰”的思辨、对“精神”与“灵魂”的探索、对人类未来奔跑路径的担忧,都与他的电影相符,因为电影是他所用的具体探索方式。也让我们看到,在平凡甚至琐碎的事情中追求“真”和“美”是可能的。本文内容来自新京报书评周刊10月24日特稿《日记中的塔可夫斯基》B02-03版。 《殉道记:塔可夫斯基日记1970-1986》 作者:安德烈·塔可夫斯基 译者:李志芳 刘西农 版本:乌托邦|云南石油奥普尔出版社2025年5月艺术是祈祷新京报:《殉道记》是塔可夫斯基的回忆录。日记与电影不同。电影是结构完整的艺术品,而日记则支离破碎、杂乱无章。总的来说,您如何看待塔可夫斯基的回忆录?它在塔可夫斯基的所有作品(电影、戏剧等)中有何独特性或特殊意义?李志芳(《殉道记》译者):在这里,我先引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解释回忆录和电影的区别。 “人们写日记几乎都是为了总结一天、一周、一个月、一个季度、一年。归根结底,都是对人生的总结。”日记不像电影,是专门拍给别人看的。日记是为我自己写的。但日记迟早会有读者,尤其是名人的日记。日记的读者感兴趣的并不是所有让作者思考和感受的事情。读者学习的日记是自然的(书面的)并且同时创作一幅自画像。塔可夫斯基的日记是这样的。他的日记记录了他后半生所经历的苦难。这种记录对于读者来说是一种认可,也是一种推广。毫不奇怪,名人日记的出版现在很受欢迎。在电影中,作者通过对人物的描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达到了一定的高度。新京报:“殉难”是一个具有崇高意义的表达方式。塔可夫斯基将他的日记命名为“殉道者”,这表明他对自己写的日记有一定的定位或希望。在本书的序言中,塔可夫斯基经常重复说:“我们的存在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的了。”如何理解他这句话的意思呢?塔可夫斯基在1970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下了他对“真理”、“上帝”、“宗教”、“哲学”、“艺术”、“无限”和“超越存在”的思考。这些想法可以指出 ev每个人都追求一种纯粹的灵性,这大概就是Ta的主要思想。你如何理解塔可夫斯基?相关想法?李志芳:日记里有一句话,“人活着不是为了追求幸福,没有什么比幸福更重要的了。”我认为最重要的是生命和责任感。艺术家的责任是关心社会发展、人类发展。艺术的责任是揭露社会的黑暗,颂扬光明。背离了这个观念,就违背了艺术家的使命,自然不会满足。也可以说,这就是塔可夫斯基的思想。然而,在体现这种责任感的意识中,似乎又遇到了困难,工作没有组织,情绪受到压抑,最后出现身体问题直至牺牲。可以说,塔可夫斯基在国外拍摄的两部电影就是他自己命运的写照。这《怀旧》结尾时演员奥列格·扬科夫斯基手中的移动蜡烛似乎成为了他的“艺术与生活”的隐喻,而“牺牲”则隐喻了他艺术生命和他自己的终结。用一位评论家的话说,塔可夫斯基的特别之处在于,他不属于“右”,也不属于“左”,与苏联体制完全不相容。后来他的移民经历表明他不适合欧洲的电影制作体系,他个人很难筹到钱拍电影。 1984年,即他去世前两年,他说:“……我知道,我必须把我的工作视为一种行动,一种被迫的行为。此时,工作不再能带来快乐,而是成为一种沉重的、甚至是压抑的责任。”在塔科夫的视野中,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祈祷形式。艺术的顶峰就是当你的祈祷能够亲近别人或者给别人带来帮助的时候,那么这个祈祷就是有益的。对他来说,“宗教是人类的精神核心”“殉道”是他对电影的发自内心的奉献。塔可夫斯基新京报:塔可夫斯基经常写到他创作电影的大环境对他的限制,如资金问题、失败的剧本、已完成的电影的大剪、发行问题等。1972年的一篇日记中写道:“这是一个多么神奇的国家。他们不想看到新的美丽的电影和美丽的书籍……毫无疑问,艺术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禁忌,因为艺术是人道的,他们的使命就是杀死一切生灵,杀死它们。”所有人文主义的萌芽,无论是人们对自由的渴望,还是黑暗地平线上闪烁的艺术之光……他们用这种方式杀死一切,毁灭自己和俄罗斯。“塔可夫斯基创作他的电影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尽管困难重重,塔可夫斯基仍能拍出如此伟大的电影,这似乎是一个奇迹。通过厂艺委会的预算项目可以分配,也是因为他的每一部电影都获奖了。或许因为他年轻有活力,有拿奖的资本,所以他势在必行。每当他申请一个项目时,他都希望得到领导的批准。即使个别项目申请不获批准而向他推荐另一个项目,他也不会同意。这是冲突的焦点。另外,当时还有电影制作补贴。凭借他的才华,他觉得自己一年可以拍两部电影。然而,目前的情况是,一部电影需要很多年才能完成,因为审查不允许它上映。这让他心里不平衡。于是,他先去找厂长,再去找局长,再去找厂长,如此循环往复,但问题并没有解决。至于他为何能够拍出这么多精彩的电影:一是他的才华;二是他的才华。其次,当时的创作环境。每部影片都经过精心制作,以免出现问题出了问题,事情就被搁置了。除了剧本内容之外,导演还投入大量精力研究镜头。无法向公众展示的isysu隐藏在镜头后面,让观众仔细思考和理解。这些东西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就派上用场了。他具有非常好的组织和指挥能力。在《安德烈·卢布廖夫》这样的大型影片中,一个人指挥数千军队与敌人作战,还有数百无数的平民。看似混乱的场面,却被导演掌控得井然有序。莫斯科电影制片厂总经理卡扬·沙赫纳扎罗夫日前在电视采访中赞扬了塔可夫斯基。拍摄现场涉及的人很多,但导演安排得井然有序。拍摄取得了成功,展示了塔可夫斯基的控制能力。这也是奇迹发生的原因。塔可夫斯基正在为《哈姆雷特》进行训练。俄罗斯北京失踪新闻a:在谈论一位创作者时,人们往往想了解他与他所处时代的关系。塔可夫斯基与他的时代有何关系?李志芳:塔可夫斯基热爱俄罗斯。他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苏联诗人,对他影响很大。虽然她和父亲不住在一起,而且父亲也反对她出国,但父亲仍然爱她,希望她经常回家,不忘家。塔可夫斯基对母亲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无论她出国之前还是之后。俄罗斯一直在他的脑海里。在日记中,我们经常看到他对俄罗斯的喜爱之情。作品中总能看到俄罗斯的影子。可惜他落后了一点。如果当俄罗斯实行改革时他还活着,也许他会回到俄罗斯。新京报:从大环境到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生活状况。日记里有很多相关的内容,这使得日记日记特别而有趣。与现在大导演的想象(如名利)不同,塔可夫斯基的个人生活相当不愉快。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的日记中经常写到债务问题。塔可夫斯基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在他的日记中,他不止一次写到“孤独”的感觉以及他与家人的关系。李志芳:这个情况我也看到了。塔可夫斯基的工资和收入和其他人一样,所以他的生活应该是相似的,但他的负担很重,显得很拥挤。更重要的是,如果他拍的电影不多,他得到的补贴就会更少。这也是他经常要求导演给他项目的原因。因为。而且,他在乡下买了房子,不能拒绝钱,所以他经常借钱。从现有资料可以看出,塔可夫斯基和普通人一样,每天过着简单的生活,从不铺张浪费。这可能是原因之一这就是为什么他渴望出国拍电影。他一直认为在欧洲拍电影更容易赚钱。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欧洲和俄罗斯的电影投资渠道不同。俄罗斯是国家资助的电影,所以当《潜行者》电影拍摄出现问题时,国家出钱重拍。意大利高度依赖机构和私人资金来筹集投资资金。如果找不到投资,就很难拍摄项目。因此,塔可夫斯基只要在意大利有空闲时间,就会拍旅游片和纪录片,赚取外快养家糊口。说到他和家人的关系,日记里写到了他和父亲的关系。自从他与第一任妻子离婚后,他的父母就有了一些意见。为了不激怒父亲,他很少去看望父母。但如果不去,他就放不下,心里还是紧张。出国前我去看望了我的父亲。两人聊得很开心。似乎过去的耻辱都解开了,心里的疙瘩也解开了。至于卡伦塔可夫斯基的电影,我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心理来理解他的。他确实是一个人,而且以他的天赋和能力,他很少尊重任何人。片场里,除了导演,没有一个不是他玩过的。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出有多少人会喜欢他?在家里,妻子关心他、照顾他,儿子疼爱他,这让他很幸福,很幸福。他很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也很爱他,这让他很幸福。质疑新京报存在:塔可夫斯基在回忆录中对“艺术家”的定义相当一致:艺术家就是追求真理的人。这个定义是一种结合“真”与“美”的表达方式,与很多现当代艺术创作者不同。如何从塔可夫斯基的作品中理解他的意义呢?刘信农(《殉教》译者)):我认为塔可夫斯基认为艺术作为一种“精神实践”很重要。他认为艺术家的使命是揭示存在的本质,而不是追求形式或感官愉悦。 《镜子》中屋顶落下的水、《牺牲》中燃烧的房屋、《怀旧》中雾气中的日出、意大利教堂废墟中出现的俄罗斯乡间别墅等场景,显然不是为了营造视觉奇观——影片中经典的长镜头、大量自然元素的运用,以及它们给人们带来的时间延伸和空间交错的幻觉,都是为了剥去幻觉。 并让观众面对存在本身。塔可夫斯基在日记和创作对话中都强调,艺术是对事物的质疑,而电影美学和技术是传达这种质疑的工具。在他的形象中,“美”从来不是与“真”对立的形式或表象,而是通向真理的一种方式。新京报:虽然塔可夫斯基致力于创造只能通过电影媒介展现的东西,他与文学的关系应该是清晰的。日记中记录了他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托马斯·曼、黑塞、松尾芭蕉、蒙田、布宁等人作品的感想,甚至摘录了一些段落。另外,塔可夫斯基的父亲阿尔西·谢尼·塔可夫斯基是一位诗人,他的诗歌对塔可夫斯基影响很大。文学给塔可夫斯基和他的电影带来了什么?刘新农:塔可夫斯基在日记中提到了无数作家的作品。除了在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巨著文学之外,他还得到了许多西方作家的强烈认可。我想单从艺术形式来看,文学无疑为他的形象叙事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作品中的道德和宗教困境实际上是《安德烈·卢布廖夫》、《太空》和《S》等电影中探讨的主题。《怀旧》中的主人公戈尔恰科夫总有一种孤独感,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不同;而《镜子》则通过非线性的结构呈现出内在的意象和章节式记忆的短片段,或许与蒙田的随想曲或芭蕉的俳句有一些美妙的呼应。 《镜子》直接记录了父亲亲口提到的那首诗,诗中的语言节奏、重复的句子和象征意象也奠定了影片的叙事节奏。我在读日记时还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在人生的不同阶段,他的阅读选择和喜好也发生了变化。当他在莫斯科,当电影创作和发行受阻时,他会反复阅读黑塞和 其他;后来离开苏联旅居意大利,登记为果戈里党员。他借的第一套书是十月革命后被流放到巴黎的布宁的日记和回忆录(老塔在日记中评价布宁:“他的小说能表达如此深沉的爱、同情、无奈和绝望”)。我想,他与其说是在这些作家身上寻找创作灵感,不如说是想从这些作家的人生轨迹中窥见自己的命运。塔可夫斯基年轻时。新京报记者:谈到塔可夫斯基的阅读,塔可夫斯基在1978年的一篇日记中列出了一份有趣的书单,其中包括《灵魂的科学》、《灵魂的不朽》和《印度哲学》。 1981 年的一篇日记写道“探索奇迹”。这些书可能暗示着塔可夫斯基精神世界的一些特征或者理解,或者他的一些激情和探索。你对此有何看法?这些特质或倾向对他在影片中的表达有影响吗?刘新农g:塔可夫斯基始终对探索强大的维度和精神知识抱有强烈的热情。我认为他试图找到一种意识形态框架来解释并体现人类的终极关切。这种阅读或许让他对自己的非理性经历更加敏感,帮助他专注于与日常生活并置的非凡经历,并最终将奇迹、救赎和宗教信仰形象化——比如《潜行者》结尾处通过视野移动事物的小女孩的轮廓,以及亚历山大为避免世界末日而进行的祭祀仪式“牺牲”。对于塔可夫斯基来说,电影是探索人类存在的意义、灵魂的命运以及救赎的可能性的媒介。这些书可以强化他对电影作为精神探索工具的信念。双重疏离 新京报:日记显示,当塔可夫斯基思考救赎和上帝时,他会写诸如“爱到爱”之类的观点。有趣的是,他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人时,有时会认为别人“浅薄幼稚”、“虚伪”、“不入世”、“平凡”、“平庸”等等。这不是对塔可夫斯基的批评,而是日记中呈现的现象。对于这种现象你怎么看?刘新农:这种冲突在他的电影中确实可以看到,主角愿意为世界牺牲自己,但每天却很难与家人在一起。这可能是一个对周围一切都抱有严格标准的艺术家性格中内在张力的一部分:他把“爱”视为他必须对他人承担的道德义务,几乎是一种宗教戒律。然而,过于理想化的道德标准和零容忍的思维,让他对“世俗”的现实过于敏感,因此在人际关系中很难摆脱失望或疏远的感觉。日常生活。新京报:如今,塔可夫斯基已被众多电影爱好者推崇至高位。他在 1981 年的日记中说道,“我仍然不明白其他地方对我的重视:意大利、法国,尤其是瑞典。他们对我表现出非凡的尊重,并对我表示连我都无法表达的赞美。为什么我不想为自己的重要性感到羞耻。”如何理解塔可夫斯基对赞扬的反应是什么?刘新农:他对外界赞扬的反应很复杂:他知道自己作品的分量,但他也不想被媒体塑造成“大师”。因为赞美和咒骂对于固定一个探索某种符号变化的创造者来说都很重要。塔可夫斯基的内省性格,加上他作为特殊历史和政治环境下的苏联艺术家的身份,也许是这些国际荣誉如此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他的反应更多的是一种自我保护的形式 - h他不想让外部叙述和公共话语剥夺他在创作中所享受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新京报:1983年,身在罗马的塔可夫斯基写道:“你无法在俄罗斯生存,你也无法在这里生存……”这似乎表明塔可夫斯基在苏联与西方世界之间存在某种问题。他为什么这么说?刘信农:塔可夫斯基晚年的“流放”不仅是政治性的,还伴随着文化和身份的撕裂——他觉得自己的创作自由受到了压制,但西方的唯物主义却被带到了他的身边。 《乡愁》中戈尔恰科夫离开意大利,也是塔可夫斯基本人所经历的双重戒备的写照。我认为他的“小镇”不是一个地理概念,而是一个能够容纳精神传统和理想信仰的乌托邦。但东方或西方可以提供这样的土地。塔可夫斯基的画作,上面写着“我永远不会看到的房子”。新京报:在在本书附录的采访中,塔可夫斯基谈到了自己的创作“我更喜欢通过隐喻来表达自己……与符号不同,隐喻没有固定的含义……隐喻更像是存在本身,是一个包含在自身内部的整体。如果你触碰它,它就会立即崩溃。”你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寓言”的含义?他的电影教会了我们什么?刘新农:在我的想象中,他的所谓“寓言”就像一个正在生长的有机体——像大雨、火、空中生长的草木、烦人的水波。影片中的自然元素所传达的丰富内涵就是自然本身。它们是存在的方式,一旦它们变得过于有趣,它们就会失去巨大的吸引力。这种“一碰就掉”的特点,要求观众放弃逻辑拆解,转而凭直觉去体验。他不希望观众将他的电影视为待破解的密码,并贴上清晰的标签每个图像都有意义。相反,他希望观众让自己沉浸在图像的流动中,体验屏幕上呈现的一切作为一种存在,并接受自己被图像和声音的节奏所消除的存在感和精神震撼。撰稿/编辑张进/校对/龚兆华/薛景宁
当前网址:https://www.g2microsystems.com//a/keji/1414.html





